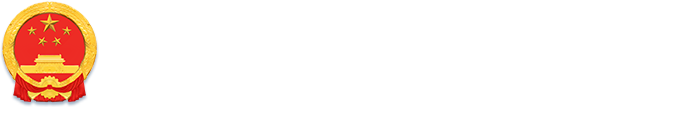李俊标作品选登——凋谢了的白兰花
发布日期:2019-05-08 00:00
来源:新城区人民政府作者简介:李俊标,满族,中共党员。历任呼和浩特新城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昭君社区副书记、呼和浩特新城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呼和浩特新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呼和浩特新城区政府办公室秘书等职。兼任呼和浩特新城区文化协会副主席、呼和浩特新城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梧桐树》杂志社记者、《边防警察》杂志社特约记者。系呼和浩特摄影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收藏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
从80年代开始新闻和文学作品业余创作,有《梦中桂花香》《春节往事》《今夜细雨为你飘》等20余万字文学作品、《山间牧场》《悄悄话》《跃马扬蹄》等1000余幅摄影作品刊发于《人民公安报》《中国边防警察》《青年月报》《内蒙古日报》《时代风纪》《梧桐树》《青少年文艺》《内蒙古青年报》《内蒙古法制报》《内蒙古晨报》《呼和浩特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北方新报》等。
先后获《呼和浩特日报》优秀副刊作者,新城区宣传报道一等奖,新城区文化工作先进个人等40多项奖励。
-----------------------------------------------------------------------------------------------------------------------------------
凋谢了的白兰花
题记:命运永远不能和一条灰白的道路相比,这是距离的秘密。当一个人把这个秘密打开,他肯定已经去了生命的尽头。
这原本不是一个落花的季节,她却无声的凋谢了,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串飘飞的花瓣和一段岁月的祭奠。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她的离去再一次深深牵动我情感的思绪,而我却至今不知她的姓名。她是一个从异乡来到内蒙古工作、生活的上海女子,在一个雨后的黄昏悄悄的以轻生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走的从从容容,没留下任何的言语和对谁的惦念……。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这个城市中央最繁华地段的一间小酒馆里,她是和刘东一起来的,刘东是我最好的朋友。在刘东把她介绍给我时,我对她的最初印象并没有多少好感,她始终爱笑,笑的不分场合、笑的开朗满足,笑的不顾及任何人。那次见面之后,我并不赞同刘东和她的交往,后来也便再很少和她见面,对她的了解更多的是在后来刘东和我的聊天中得知。她原本在上海有着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为了心中的白马王子,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埋怨,舍弃安逸的生活只身来到了呼和浩特,死心塌地的和那个男子结了婚。婚后的第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她丈夫竟然有了婚外情,当她体验到了丈夫对她失却新鲜后的冷漠,以及亲人对她的不解和责备后,变的一蹶不振,她慢慢明白,在婚姻道路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不可及,让从小生活在亲情溺爱环境中的她,感受到了无助和孤独。在呼和浩特她没有一个朋友,她如一叶漂移在大洋深处的孤舟,孤零零的整日把自己关在家中,爱好读书的她不再喜欢图书馆的静谧,酒吧和迪厅的喧嚣帮她打发了许多郁闷和消沉,但却无法使她重新振作起来。刘东的出现让她的生活或多或少有了新的色彩。刚从国外读书回来的刘东在一家外语学校任教,和她的认识是在朋友的一次聚会上,少言寡语的刘东和她坐在一起,两个人默默的听着别人的谈笑,不时的用眼睛注视着对方,也许是性情相投的缘故,聚会结束后刘东邀她走进了一间咖啡屋,整个下午,她把自己所有的心事竟一股脑的全部告诉了刘东,直听的刘东生生的掉下了眼泪,刘东为她的故事在惋惜中滋生出了许多的怜悯。后来,刘东和她成了特别好的朋友,她大刘东5岁,虽然他们彼此知道这是一段不符合实际的恋情,但年龄并没有阻碍了他们的交往。那些日子,刘东除去上班,多数时间里陪她逛街、看电影。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日子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半年后的一天,在上海的父母因家中有事需要她回去住一段时间,接到父母电话,本来打算回去后再告诉刘东,但她还是在候车室里给刘东发了短信。那时侯,刘东正在上课,看到短信,刘东心慌意乱的好不容易挨到下课,就飞一样的赶往车站,就在刘东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动了,隔着车窗两个人像是生离死别一样拼命的呼喊着对方的名字。

她回上海后不久,刘东因工作关系也调离呼市去了宁夏。刘东到了新的单位后,因为诚实肯干的缘故,很快受到领导的重视,把他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岗位上,这样,刘东整天忙的焦头烂额,有时候连吃饭的工夫都很难空出来,时间一长,他俩联系的时间逐渐少了起来,以至她什么时候从上海回到呼和浩特刘东都没有知情。一次,刘东回呼和浩特办事,才知道她已回来。那天,他们在一起整整呆了一个晚上,谈了很多很多,她说不想再不切实际的这样活下去,她要好好面对生活,并打算到国外上学。后来的日子,她和刘东依然时常通话,但谁也不再提及情感之类的话题。一天下午,刘东正在单位开会,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她笑着对刘东说,她活的太累了,她想到了死,但死之前她希望见刘东最后一面。听完她的话,刘东生气的狠狠的训了她一番,她没有吱声,只是一个劲的又哭又笑。通完话后,刘东没有在意,想到她最近的心情不好,认为是在闹着玩。可就在那天,她真的割腕自杀,所幸被家人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

刘东怎么也没想到她对生活如此自暴自弃。
后来的日子,她一心投入到了为出国做准备的学习上,整天把自己关在家中拼命的学习外语,刘东还几次通过朋友从国外给她带回不少的学习资料,并托我给她捎去,每次送书见到她时,感觉她像换了个人似的,文文静静,全然没有最初对她的印象,她也曾邀请我到她家坐坐,我只客气的把书交到她的手中,转达了刘东的意思后就离开了。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市中心一家精神病院二层小楼的病床上。那天,刘东急匆匆的从宁夏赶回呼和浩特要我陪他去医院看一个朋友,到了医院后我才知道是她。病床上她笑容依旧,但面色憔悴、精神恍惚,她对我的来访表现出一种不悦的情绪,这与我最初认识她时的样子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如何也想不出这样一个快乐的女子背后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景况。从医院出来后,我把刘东送到回宁夏的车上,刘东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她活的太累,太苦了”,而我并没有在意刘东言语后的寓意,只是第一次看到了他朦胧的泪眼,我一个劲地责备刘东,“不要那么婆婆妈妈,别在自欺欺人的感情中迷失了,好好工作”。后来得知,她出国的愿望最后在她丈夫的阻拦下并没有实现,为此她们家闹了个天翻地覆,还差一点离了婚,她的父母专程从北京赶来住了一段时间,在她父母的劝慰下总算平息了这件事。

日子在无声的流逝,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的忙碌中操持着,这段如花瓣一样飘飞的故事,也慢慢的淡忘在繁杂的日子里。那天,我突然接到了刘东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刘东微泣着告诉了我一个震惊的消息——她自杀了。我漠然,她怎么能如此轻易的舍去这个世界,她应该活着。但对于她的死,我没有过多的去追问因果。放下了刘东的电话,我突然感到了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已经开始让人窒息,让我们无法痛快的呼吸自由的养分。我们都在社会生存的重压下挣扎,企求生活的宽容。
她的离去,或许对她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可以看作是舞台上的舞者在音乐中谢幕后,未及退去舞衣,辉煌已随舞台灯光熄灭的一刹那随之而去,留给别人的只是布满灰尘的昨天。不需要依恋和长久的追问。我相信刘东以及她家人的伤悲和痛楚,在时间的推移中会渐渐转为平和,而她的死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为触动心灵的标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我们脚下的路和我们所期待的来自岁月的回声。
文章没有定义的开头,也不会有婉转的收尾,在细雨纷飞的清明节,我想到了她,提笔去纪念她,其本意是劝慰我的朋友或是告慰已经离去的她。她的离去不论是何种原由,我想,她在天堂的那端应该会寻找到一个好的归属。我也冒昧的以“白兰花”做了对她的称谓。
希望她能喜欢,我没有别的祭语!
作者简介:李俊标,满族,中共党员。历任呼和浩特新城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昭君社区副书记、呼和浩特新城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呼和浩特新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呼和浩特新城区政府办公室秘书等职。兼任呼和浩特新城区文化协会副主席、呼和浩特新城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梧桐树》杂志社记者、《边防警察》杂志社特约记者。系呼和浩特摄影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收藏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
从80年代开始新闻和文学作品业余创作,有《梦中桂花香》《春节往事》《今夜细雨为你飘》等20余万字文学作品、《山间牧场》《悄悄话》《跃马扬蹄》等1000余幅摄影作品刊发于《人民公安报》《中国边防警察》《青年月报》《内蒙古日报》《时代风纪》《梧桐树》《青少年文艺》《内蒙古青年报》《内蒙古法制报》《内蒙古晨报》《呼和浩特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北方新报》等。
先后获《呼和浩特日报》优秀副刊作者,新城区宣传报道一等奖,新城区文化工作先进个人等40多项奖励。
-----------------------------------------------------------------------------------------------------------------------------------
凋谢了的白兰花
题记:命运永远不能和一条灰白的道路相比,这是距离的秘密。当一个人把这个秘密打开,他肯定已经去了生命的尽头。
这原本不是一个落花的季节,她却无声的凋谢了,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串飘飞的花瓣和一段岁月的祭奠。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她的离去再一次深深牵动我情感的思绪,而我却至今不知她的姓名。她是一个从异乡来到内蒙古工作、生活的上海女子,在一个雨后的黄昏悄悄的以轻生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走的从从容容,没留下任何的言语和对谁的惦念……。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这个城市中央最繁华地段的一间小酒馆里,她是和刘东一起来的,刘东是我最好的朋友。在刘东把她介绍给我时,我对她的最初印象并没有多少好感,她始终爱笑,笑的不分场合、笑的开朗满足,笑的不顾及任何人。那次见面之后,我并不赞同刘东和她的交往,后来也便再很少和她见面,对她的了解更多的是在后来刘东和我的聊天中得知。她原本在上海有着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为了心中的白马王子,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埋怨,舍弃安逸的生活只身来到了呼和浩特,死心塌地的和那个男子结了婚。婚后的第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她丈夫竟然有了婚外情,当她体验到了丈夫对她失却新鲜后的冷漠,以及亲人对她的不解和责备后,变的一蹶不振,她慢慢明白,在婚姻道路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不可及,让从小生活在亲情溺爱环境中的她,感受到了无助和孤独。在呼和浩特她没有一个朋友,她如一叶漂移在大洋深处的孤舟,孤零零的整日把自己关在家中,爱好读书的她不再喜欢图书馆的静谧,酒吧和迪厅的喧嚣帮她打发了许多郁闷和消沉,但却无法使她重新振作起来。刘东的出现让她的生活或多或少有了新的色彩。刚从国外读书回来的刘东在一家外语学校任教,和她的认识是在朋友的一次聚会上,少言寡语的刘东和她坐在一起,两个人默默的听着别人的谈笑,不时的用眼睛注视着对方,也许是性情相投的缘故,聚会结束后刘东邀她走进了一间咖啡屋,整个下午,她把自己所有的心事竟一股脑的全部告诉了刘东,直听的刘东生生的掉下了眼泪,刘东为她的故事在惋惜中滋生出了许多的怜悯。后来,刘东和她成了特别好的朋友,她大刘东5岁,虽然他们彼此知道这是一段不符合实际的恋情,但年龄并没有阻碍了他们的交往。那些日子,刘东除去上班,多数时间里陪她逛街、看电影。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日子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半年后的一天,在上海的父母因家中有事需要她回去住一段时间,接到父母电话,本来打算回去后再告诉刘东,但她还是在候车室里给刘东发了短信。那时侯,刘东正在上课,看到短信,刘东心慌意乱的好不容易挨到下课,就飞一样的赶往车站,就在刘东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动了,隔着车窗两个人像是生离死别一样拼命的呼喊着对方的名字。

她回上海后不久,刘东因工作关系也调离呼市去了宁夏。刘东到了新的单位后,因为诚实肯干的缘故,很快受到领导的重视,把他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岗位上,这样,刘东整天忙的焦头烂额,有时候连吃饭的工夫都很难空出来,时间一长,他俩联系的时间逐渐少了起来,以至她什么时候从上海回到呼和浩特刘东都没有知情。一次,刘东回呼和浩特办事,才知道她已回来。那天,他们在一起整整呆了一个晚上,谈了很多很多,她说不想再不切实际的这样活下去,她要好好面对生活,并打算到国外上学。后来的日子,她和刘东依然时常通话,但谁也不再提及情感之类的话题。一天下午,刘东正在单位开会,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她笑着对刘东说,她活的太累了,她想到了死,但死之前她希望见刘东最后一面。听完她的话,刘东生气的狠狠的训了她一番,她没有吱声,只是一个劲的又哭又笑。通完话后,刘东没有在意,想到她最近的心情不好,认为是在闹着玩。可就在那天,她真的割腕自杀,所幸被家人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

刘东怎么也没想到她对生活如此自暴自弃。
后来的日子,她一心投入到了为出国做准备的学习上,整天把自己关在家中拼命的学习外语,刘东还几次通过朋友从国外给她带回不少的学习资料,并托我给她捎去,每次送书见到她时,感觉她像换了个人似的,文文静静,全然没有最初对她的印象,她也曾邀请我到她家坐坐,我只客气的把书交到她的手中,转达了刘东的意思后就离开了。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市中心一家精神病院二层小楼的病床上。那天,刘东急匆匆的从宁夏赶回呼和浩特要我陪他去医院看一个朋友,到了医院后我才知道是她。病床上她笑容依旧,但面色憔悴、精神恍惚,她对我的来访表现出一种不悦的情绪,这与我最初认识她时的样子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如何也想不出这样一个快乐的女子背后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景况。从医院出来后,我把刘东送到回宁夏的车上,刘东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她活的太累,太苦了”,而我并没有在意刘东言语后的寓意,只是第一次看到了他朦胧的泪眼,我一个劲地责备刘东,“不要那么婆婆妈妈,别在自欺欺人的感情中迷失了,好好工作”。后来得知,她出国的愿望最后在她丈夫的阻拦下并没有实现,为此她们家闹了个天翻地覆,还差一点离了婚,她的父母专程从北京赶来住了一段时间,在她父母的劝慰下总算平息了这件事。

日子在无声的流逝,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的忙碌中操持着,这段如花瓣一样飘飞的故事,也慢慢的淡忘在繁杂的日子里。那天,我突然接到了刘东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刘东微泣着告诉了我一个震惊的消息——她自杀了。我漠然,她怎么能如此轻易的舍去这个世界,她应该活着。但对于她的死,我没有过多的去追问因果。放下了刘东的电话,我突然感到了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已经开始让人窒息,让我们无法痛快的呼吸自由的养分。我们都在社会生存的重压下挣扎,企求生活的宽容。
她的离去,或许对她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可以看作是舞台上的舞者在音乐中谢幕后,未及退去舞衣,辉煌已随舞台灯光熄灭的一刹那随之而去,留给别人的只是布满灰尘的昨天。不需要依恋和长久的追问。我相信刘东以及她家人的伤悲和痛楚,在时间的推移中会渐渐转为平和,而她的死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为触动心灵的标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我们脚下的路和我们所期待的来自岁月的回声。
文章没有定义的开头,也不会有婉转的收尾,在细雨纷飞的清明节,我想到了她,提笔去纪念她,其本意是劝慰我的朋友或是告慰已经离去的她。她的离去不论是何种原由,我想,她在天堂的那端应该会寻找到一个好的归属。我也冒昧的以“白兰花”做了对她的称谓。
希望她能喜欢,我没有别的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