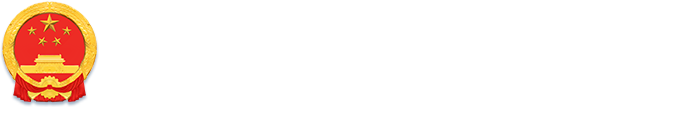李俊标作品选登——蒸寒燕
发布日期:2019-04-12 00:00
来源:新城区人民政府作者简介:李俊标,满族,中共党员。历任呼和浩特新城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昭君社区副书记、呼和浩特新城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呼和浩特新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呼和浩特新城区政府办公室秘书等职。兼任呼和浩特新城区文化协会副主席、呼和浩特新城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梧桐树》杂志社记者、《边防警察》杂志社特约记者。系呼和浩特摄影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收藏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
从80年代开始新闻和文学作品业余创作,有《梦中桂花香》《春节往事》《今夜细雨为你飘》等20余万字文学作品、《山间牧场》《悄悄话》《跃马扬蹄》等1000余幅摄影作品刊发于《人民公安报》《中国边防警察》《青年月报》《内蒙古日报》《时代风纪》《梧桐树》《青少年文艺》《内蒙古青年报》《内蒙古法制报》《内蒙古晨报》《呼和浩特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北方新报》等。
先后获《呼和浩特日报》优秀副刊作者,新城区宣传报道一等奖,新城区文化工作先进个人等40多项奖励。
----------------------------------------------------------------------------------------------------------------------------------------
蒸寒燕
小时候,家乡有“蒸寒燕”的习俗。
每年早春时节,母亲总会用白面捏出许多如核桃大小,型如燕子、小鸡之类的小动物。蒸熟后,在这些“小动物”的身上用颜料点上五颜六色的色彩,然后找来枸杞枝或是带刺的植物枝插在上面,拿到屋檐下晾晒。这些晾干的面食就是 “寒燕”。那个年代,生活在乡下的孩子一年四季见不到什么零食,“寒燕”便是最好的美味。等到“寒燕”晾干可以吃的时候,我们每天都磨着母亲问,是不是可以吃了,每次母亲都会露出慈爱的笑容,轻声的说一句:“小馋猫”,然后再从屋檐下摘下几个“寒燕”递到我们手上。取下的“寒燕”我们却总舍不得吃,放在书包里,吃的时候也是先在“小燕子”的翅膀或头上轻轻咬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的啃。所以,这对孩子们来说,手里的“寒燕”总是残缺不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年春天,又到了捏“寒燕”的季节,我早早地守在了母亲身边,等着她为我捏“寒燕”。那段日子,好赌的父亲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往家拿工资,输的连家里买面的钱都没有。母亲看着我乞渴的样子,拿起空空的面袋对我说,家里现在没有白面了,过几天买来白面一定给你捏。第二天一早,邻居家的几个孩子站到我家窑洞的窗户前,喊我一起出去玩,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几个“寒燕”。我极其羡慕的看着他们手里散发着诱人面香的“寒燕”,一把揪住了母亲的衣襟,磨着她为我捏“寒燕”。母亲一声不吭地坐在土炕上做着针线活儿,我很快从央求转为啕哭,母亲突然一把拉过我,在我的屁股上狠狠打了几下,母亲的惩戒非但没有让我停止哭闹,我进而扑倒在她的脚下,不依不饶的哭个没完。过了好一会儿,母亲将我从地上抱起一把搂在怀里,无奈的泪水顺着衣衫滚落到了我的脸上。母亲边擦着我脸上的泪水边慢声细语的哄着我,答应等过些日子买了白面一定捏好多好多的“寒燕”。母亲的劝慰还是没有制止我无知的咆哮,我的哭声歇斯底里的响彻了那个下午我家住着的窑洞。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最后我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我醒来后,我看到在窑洞的土炕上放着两个对扣着的瓷碗。翻起扣在上面的碗,两只色泽金黄透亮、散发着醇香的炒鸡蛋卧在碗底。鸡蛋虽然很少,但浓浓的香气早已挂满了我的鼻尖。“这是你最爱吃的炒鸡蛋,吃吧”,母亲深情的说。早已饥肠辘辘的我顾不了许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一刻,我分明看见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酸涩的笑容。那是此生我吃过的最香的一碗炒鸡蛋。几年后,我偶然得知,那次是母亲在我睡熟后跑到一家认识的供销社里赊来两只鸡蛋,用家里仅剩的一点猪油为我炒的。
那年,我五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因病早早的离开了我们。在我清晰的记忆里,那碗炒鸡蛋和那些当今孩子们不曾认知的“寒燕”一样时常会萦绕在我的梦里,让我怀念、让我哭泣,那是母性的善良和一个孩子对世俗无知的顽淘。如今,无论在哪里吃饭,我总会点一盘炒鸡蛋,尽管已经无法再次用嗅觉去体味那种渗透着情愫的香气。因为我知道,记忆中的醇香永不再有。
作者简介:李俊标,满族,中共党员。历任呼和浩特新城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昭君社区副书记、呼和浩特新城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呼和浩特新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呼和浩特新城区政府办公室秘书等职。兼任呼和浩特新城区文化协会副主席、呼和浩特新城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梧桐树》杂志社记者、《边防警察》杂志社特约记者。系呼和浩特摄影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收藏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
从80年代开始新闻和文学作品业余创作,有《梦中桂花香》《春节往事》《今夜细雨为你飘》等20余万字文学作品、《山间牧场》《悄悄话》《跃马扬蹄》等1000余幅摄影作品刊发于《人民公安报》《中国边防警察》《青年月报》《内蒙古日报》《时代风纪》《梧桐树》《青少年文艺》《内蒙古青年报》《内蒙古法制报》《内蒙古晨报》《呼和浩特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北方新报》等。
先后获《呼和浩特日报》优秀副刊作者,新城区宣传报道一等奖,新城区文化工作先进个人等40多项奖励。
----------------------------------------------------------------------------------------------------------------------------------------
蒸寒燕
小时候,家乡有“蒸寒燕”的习俗。
每年早春时节,母亲总会用白面捏出许多如核桃大小,型如燕子、小鸡之类的小动物。蒸熟后,在这些“小动物”的身上用颜料点上五颜六色的色彩,然后找来枸杞枝或是带刺的植物枝插在上面,拿到屋檐下晾晒。这些晾干的面食就是 “寒燕”。那个年代,生活在乡下的孩子一年四季见不到什么零食,“寒燕”便是最好的美味。等到“寒燕”晾干可以吃的时候,我们每天都磨着母亲问,是不是可以吃了,每次母亲都会露出慈爱的笑容,轻声的说一句:“小馋猫”,然后再从屋檐下摘下几个“寒燕”递到我们手上。取下的“寒燕”我们却总舍不得吃,放在书包里,吃的时候也是先在“小燕子”的翅膀或头上轻轻咬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的啃。所以,这对孩子们来说,手里的“寒燕”总是残缺不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年春天,又到了捏“寒燕”的季节,我早早地守在了母亲身边,等着她为我捏“寒燕”。那段日子,好赌的父亲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往家拿工资,输的连家里买面的钱都没有。母亲看着我乞渴的样子,拿起空空的面袋对我说,家里现在没有白面了,过几天买来白面一定给你捏。第二天一早,邻居家的几个孩子站到我家窑洞的窗户前,喊我一起出去玩,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几个“寒燕”。我极其羡慕的看着他们手里散发着诱人面香的“寒燕”,一把揪住了母亲的衣襟,磨着她为我捏“寒燕”。母亲一声不吭地坐在土炕上做着针线活儿,我很快从央求转为啕哭,母亲突然一把拉过我,在我的屁股上狠狠打了几下,母亲的惩戒非但没有让我停止哭闹,我进而扑倒在她的脚下,不依不饶的哭个没完。过了好一会儿,母亲将我从地上抱起一把搂在怀里,无奈的泪水顺着衣衫滚落到了我的脸上。母亲边擦着我脸上的泪水边慢声细语的哄着我,答应等过些日子买了白面一定捏好多好多的“寒燕”。母亲的劝慰还是没有制止我无知的咆哮,我的哭声歇斯底里的响彻了那个下午我家住着的窑洞。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最后我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我醒来后,我看到在窑洞的土炕上放着两个对扣着的瓷碗。翻起扣在上面的碗,两只色泽金黄透亮、散发着醇香的炒鸡蛋卧在碗底。鸡蛋虽然很少,但浓浓的香气早已挂满了我的鼻尖。“这是你最爱吃的炒鸡蛋,吃吧”,母亲深情的说。早已饥肠辘辘的我顾不了许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一刻,我分明看见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酸涩的笑容。那是此生我吃过的最香的一碗炒鸡蛋。几年后,我偶然得知,那次是母亲在我睡熟后跑到一家认识的供销社里赊来两只鸡蛋,用家里仅剩的一点猪油为我炒的。
那年,我五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因病早早的离开了我们。在我清晰的记忆里,那碗炒鸡蛋和那些当今孩子们不曾认知的“寒燕”一样时常会萦绕在我的梦里,让我怀念、让我哭泣,那是母性的善良和一个孩子对世俗无知的顽淘。如今,无论在哪里吃饭,我总会点一盘炒鸡蛋,尽管已经无法再次用嗅觉去体味那种渗透着情愫的香气。因为我知道,记忆中的醇香永不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