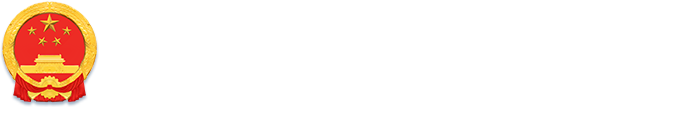高欢、斛律金和大青山
发布日期:2018-01-17 00:00
来源:新城区人民政府高欢:《敕勒歌》流传千古的肇创者
斛律金:《敕勒歌》的形象推广大使
大青山:高欢的诞生地和斛律金的工作地
大青山:《敕勒歌》中的乡愁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苍穹,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上至80岁老翁下至3岁孩童都耳熟能详的《敕勒歌》,寥寥27个字描绘出一幅宏大壮美、催人遐想的史诗画卷:苍茫辽阔的敕勒川平原水草丰美、碧草连天、香气袭人,片片白云在无尽的蓝天中飘游,牧人策马、牛羊游动,再加上蒙古包缕缕的炊烟与缓缓行驶的勒勒车,这种古代北方牧民浪漫祥和的悠哉生活,引得无数文人志士“此生梦断封侯想,也到阴山敕勒川”,更是现代都市人苦苦追寻的“世外桃源”和浓浓乡愁。
《敕勒歌》中的“阴山”主要指现今阴山山脉中段的大青山,东起呼和浩特大黑河上游谷地,西至包头昆都仑河,东西长240多公里,南北宽20~60公里。这座神奇地穿梭于中国农耕和游牧经济交汇处的大山,虽然很多时候并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龙兴之地,但却是这些民族逐鹿中原的跳板、走向辉煌的胜地。中国历史上首个一统大漠南北的巨无霸游牧部落——匈奴正是从“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大青山(阴山)崭露头角,“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一度成为中原王朝最大的心腹大患。

而当匈奴被汉武帝彻底赶到漠北、元气大伤之后,中原王朝的另一个强邻——拓跋鲜卑便趁势南下了。这个据说在遥远的古代从西伯利亚迁徙到大兴安岭嘎仙洞的游牧部落,最早臣服于匈奴,后投靠汉朝。大约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他们历经艰难西进南迁,于3世纪中叶跨过大青山进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山西、河北北部,迅速抢占了匈奴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公元386年,一代枭雄拓跋珪创建北魏,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12年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95年后又迁都洛阳,完成了北方民族自匈奴以来所未能完成的中国北部统一大业。

《敕勒歌》中的“敕勒”,又名狄历、铁勒、丁零、高车、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的主要族源。《魏书·高车列传》载:“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敕勒人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汉朝击溃北匈奴之后,敕勒的地域开始南移。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他们频繁活动于大漠南北,对北魏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北魏统治阶级多次攻打敕勒各部,得胜后将数十万敕勒部众“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北史·高车传》)。敕勒人依靠这些地区的良好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使这里出现了一派繁荣兴旺景象。《魏书》记载:“高宗(即文成帝)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声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由于漠南地区当时主要是敕勒人聚居的地方,从此,大青山以南平原遂有“敕勒川”之称。
《敕勒歌》的最早吟唱者,据《北齐书·神武纪》记载,是东魏名将斛律金,这也是关于敕勒歌的最早记载。斛律金(488-567),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今山西朔州城区、平鲁区一带)。他生于南北朝北魏时期,高祖是当时敕勒有名的部落首领倍侯利。《魏书》记载说:“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阵,有异于众,北方人畏之。”当时的北方人每逢婴儿啼哭,只要说:“倍侯利来了!”婴儿立即停止啼哭。斛律金的祖父、父亲都在北魏政府中任很高的官职,屡立战功。斛律金曾被北魏政府任命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到京城朝见,春天又回到部落,号称“雁臣”。他擅长骑射,善于用兵,“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北齐书》)。斛律金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历任咸阳郡王、相国、太尉公、录尚书、朔州刺史等官职。值得一提的是,为防蠕蠕侵犯边塞,斛律金曾任白道守将,可见,他和大青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鲜为人知的是,那首令人神怡、催人遐想的《敕勒歌》,背后竟是一场极其惨烈、极其悲壮的玉壁之战,交战双方的核心人物就是东魏丞相高欢和西魏守将韦孝宽。
说起高欢,他是权倾一时的东魏权臣、北齐王朝奠基人,史称齐神武帝。据《北齐书·神武纪》,因祖父高谧犯法获罪,遭流放而定居到了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到其不务正业的父亲高树时,又移居大青山白道南侧,因此,高欢是地地道道的大青山人。他们居住的白道曾多次出现过赤光紫气,邻近的人们认为是灾祸作怪,劝他搬家避害,可高树却说:“这难道不是吉兆?”依然住在此地未动。大青山这座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神奇大山,造就了这位傲领华夏、冠绝古今的一代枭雄。《北史》记载:“神武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正是从大青山出发,出身孤弱、恰逢乱世的高欢开始了他从六镇戍卒到东魏主宰、征战诡谲的传奇一生。
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敕勒歌》的题目下引唐吴兢的《乐府广题》说:
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卜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546年,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神武高欢本纪下》,唐李延寿《北史》卷六《齐本纪上》。是时,东魏两次打败西魏,想借着胜利的有利时机,一举消灭西魏政权。掌握东魏大权的大丞相、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亲率大军向西魏前沿阵地玉壁城(今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市北部稷山)挺进,想攻下玉壁后,再直捣长安,一举消灭西魏。
玉壁城始建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城周八里,四面并临深谷”,形势突兀,位置险要,进可长驱突击,退可守险无虞,是西魏抵御东魏的军事前沿重镇,是西魏保关中、攻并州、灭东魏的桥头堡,也是西魏插进东魏统治区的一把利刃。于是乎,高欢亲率二十万大军,誓要拔掉这颗阻碍东魏向西扩张的钉子。但让踌躇满志的高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将是他人生的“滑铁卢”。
据史籍记载,在两个月“昼夜不息”的围攻中,高欢采用了堆砌土山、射手狙击、声东击西、截断水源、凿挖地道、战车冲撞、涂油点火等多种战术,整个军事进攻涉及高空、地面、地道三个方位,其战略思想和围攻措施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但在西魏守将韦孝宽“人在城在”般的誓死防守下,高欢采用的所有战术均被一一化解,即“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

无奈之下,高欢又派人往城中射入书信道:“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企图以重赏来瓦解西魏军心。韦孝宽得到书信后,在背面写道:“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以此来回敬了高欢。一计不成,高欢又把韦孝宽的侄儿押至城下,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向城内高喊若不投降,就要杀死他。韦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人有死难之心”,从而更加坚定不移了西魏士卒与城共存亡的信念。
高欢苦战了近六十天,丝毫不能撼动玉壁城。由于伤亡惨重,一筹莫展,加上天气寒冷,给养不足,消耗惨重。高欢“智力俱困”,只得班师晋阳。想到七万将士命丧城下,“聚为一冢”;想到原本凯旋后的庆功酒,将被讥讽声所替代;这种视觉上的血腥冲击和精神上的高压态势,使高欢愤恚成疾,一病不起。这时,韦孝宽又制造了高欢中箭身亡的谣言。为了稳定军心,高欢不得不带病“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这就是《敕勒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日食日,52岁的高欢发出“日蚀其为我耶,死亦何恨”的感慨,一代枭雄竟在窝火和重病中与世长辞。最终西魏以少胜多,并由此从弱走强,国力大盛,以西魏为基础建立了北周,又以北周为基础建立了隋,最终平灭北齐、南梁,结束三朝鼎峙。
有一个问题是,“博得后人极端的倾倒”(郑振铎语)的《敕勒歌》,到底是不是斛律金的首创?对此,《乐府广题》认为不是由斛律金所作,斛律金只是翻唱者。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大会上时讲话:“北朝的将军斛律金,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既“不读书”、又“不识文字”的斛律金,是不大可能创作出《敕勒歌》的,但他却是《敕勒歌》能够流传千古的最大功臣。宋代学者王灼《碧鸡漫志》就说,“金不知书,能发挥自然之妙如此”。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则评价为:“莽莽而来,自然高古”。元代著名回族诗人丁鹤年有感于此,乃赋诗一首:“神龙归卧北溟波,愁绝阴山《敕勒歌》。惟有遗珠光夺目,万年留得照山河”(《鹤年诗集》卷二《敬书宸翰后》)。诗中所说的“神龙”就是指神武帝高欢。很显然,高欢是想用这首歌颂家乡的歌曲以安定军心,激励斗志。但在客观上,使这首民歌得以记载并流传下来。
穿越1600年的历史时空,天籁之音《敕勒歌》至今仍传唱不衰。耐人寻味的是,大青山并没有因《敕勒歌》而名扬天下,而敕勒川却声名鹊起、名声大噪。但历来为兵家必争的大青山及其脚下的沃土敕勒川,饱经无数次硝烟烽火的蹂躏和沧桑岁月的洗礼,展现出的早已不是那水草丰美、天野相接、香气袭人、牛羊游动的亮丽风景,而是“大漠天低四野园,黄沙千里绝人烟”(余正酉《出塞绝句》)的悲催图景。进入新世纪,一场旨在恢复大青山生态外衣、重振绿水青山的战斗打响了,史无前例的生态建设大幕由此拉开。现在,走进大青山前坡150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四周的绿齐刷刷压过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历史画卷在新时代重新呈现,这或许是对千古枭雄高欢和一代名将斛律金的最大慰藉。我们还需做的是,深入挖掘隐藏在《敕勒歌》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敕勒川文化,让举世闻名的《敕勒歌》在其发源地真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名至实归!
民族宗教局 赵紫阳 供稿
高欢:《敕勒歌》流传千古的肇创者
斛律金:《敕勒歌》的形象推广大使
大青山:高欢的诞生地和斛律金的工作地
大青山:《敕勒歌》中的乡愁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苍穹,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上至80岁老翁下至3岁孩童都耳熟能详的《敕勒歌》,寥寥27个字描绘出一幅宏大壮美、催人遐想的史诗画卷:苍茫辽阔的敕勒川平原水草丰美、碧草连天、香气袭人,片片白云在无尽的蓝天中飘游,牧人策马、牛羊游动,再加上蒙古包缕缕的炊烟与缓缓行驶的勒勒车,这种古代北方牧民浪漫祥和的悠哉生活,引得无数文人志士“此生梦断封侯想,也到阴山敕勒川”,更是现代都市人苦苦追寻的“世外桃源”和浓浓乡愁。
《敕勒歌》中的“阴山”主要指现今阴山山脉中段的大青山,东起呼和浩特大黑河上游谷地,西至包头昆都仑河,东西长240多公里,南北宽20~60公里。这座神奇地穿梭于中国农耕和游牧经济交汇处的大山,虽然很多时候并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龙兴之地,但却是这些民族逐鹿中原的跳板、走向辉煌的胜地。中国历史上首个一统大漠南北的巨无霸游牧部落——匈奴正是从“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大青山(阴山)崭露头角,“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一度成为中原王朝最大的心腹大患。

而当匈奴被汉武帝彻底赶到漠北、元气大伤之后,中原王朝的另一个强邻——拓跋鲜卑便趁势南下了。这个据说在遥远的古代从西伯利亚迁徙到大兴安岭嘎仙洞的游牧部落,最早臣服于匈奴,后投靠汉朝。大约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他们历经艰难西进南迁,于3世纪中叶跨过大青山进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山西、河北北部,迅速抢占了匈奴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公元386年,一代枭雄拓跋珪创建北魏,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12年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95年后又迁都洛阳,完成了北方民族自匈奴以来所未能完成的中国北部统一大业。

《敕勒歌》中的“敕勒”,又名狄历、铁勒、丁零、高车、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的主要族源。《魏书·高车列传》载:“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敕勒人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汉朝击溃北匈奴之后,敕勒的地域开始南移。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他们频繁活动于大漠南北,对北魏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北魏统治阶级多次攻打敕勒各部,得胜后将数十万敕勒部众“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北史·高车传》)。敕勒人依靠这些地区的良好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使这里出现了一派繁荣兴旺景象。《魏书》记载:“高宗(即文成帝)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声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由于漠南地区当时主要是敕勒人聚居的地方,从此,大青山以南平原遂有“敕勒川”之称。
《敕勒歌》的最早吟唱者,据《北齐书·神武纪》记载,是东魏名将斛律金,这也是关于敕勒歌的最早记载。斛律金(488-567),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今山西朔州城区、平鲁区一带)。他生于南北朝北魏时期,高祖是当时敕勒有名的部落首领倍侯利。《魏书》记载说:“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阵,有异于众,北方人畏之。”当时的北方人每逢婴儿啼哭,只要说:“倍侯利来了!”婴儿立即停止啼哭。斛律金的祖父、父亲都在北魏政府中任很高的官职,屡立战功。斛律金曾被北魏政府任命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到京城朝见,春天又回到部落,号称“雁臣”。他擅长骑射,善于用兵,“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北齐书》)。斛律金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历任咸阳郡王、相国、太尉公、录尚书、朔州刺史等官职。值得一提的是,为防蠕蠕侵犯边塞,斛律金曾任白道守将,可见,他和大青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鲜为人知的是,那首令人神怡、催人遐想的《敕勒歌》,背后竟是一场极其惨烈、极其悲壮的玉壁之战,交战双方的核心人物就是东魏丞相高欢和西魏守将韦孝宽。
说起高欢,他是权倾一时的东魏权臣、北齐王朝奠基人,史称齐神武帝。据《北齐书·神武纪》,因祖父高谧犯法获罪,遭流放而定居到了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到其不务正业的父亲高树时,又移居大青山白道南侧,因此,高欢是地地道道的大青山人。他们居住的白道曾多次出现过赤光紫气,邻近的人们认为是灾祸作怪,劝他搬家避害,可高树却说:“这难道不是吉兆?”依然住在此地未动。大青山这座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神奇大山,造就了这位傲领华夏、冠绝古今的一代枭雄。《北史》记载:“神武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正是从大青山出发,出身孤弱、恰逢乱世的高欢开始了他从六镇戍卒到东魏主宰、征战诡谲的传奇一生。
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敕勒歌》的题目下引唐吴兢的《乐府广题》说:
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卜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546年,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神武高欢本纪下》,唐李延寿《北史》卷六《齐本纪上》。是时,东魏两次打败西魏,想借着胜利的有利时机,一举消灭西魏政权。掌握东魏大权的大丞相、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亲率大军向西魏前沿阵地玉壁城(今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市北部稷山)挺进,想攻下玉壁后,再直捣长安,一举消灭西魏。
玉壁城始建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城周八里,四面并临深谷”,形势突兀,位置险要,进可长驱突击,退可守险无虞,是西魏抵御东魏的军事前沿重镇,是西魏保关中、攻并州、灭东魏的桥头堡,也是西魏插进东魏统治区的一把利刃。于是乎,高欢亲率二十万大军,誓要拔掉这颗阻碍东魏向西扩张的钉子。但让踌躇满志的高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将是他人生的“滑铁卢”。
据史籍记载,在两个月“昼夜不息”的围攻中,高欢采用了堆砌土山、射手狙击、声东击西、截断水源、凿挖地道、战车冲撞、涂油点火等多种战术,整个军事进攻涉及高空、地面、地道三个方位,其战略思想和围攻措施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但在西魏守将韦孝宽“人在城在”般的誓死防守下,高欢采用的所有战术均被一一化解,即“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

无奈之下,高欢又派人往城中射入书信道:“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企图以重赏来瓦解西魏军心。韦孝宽得到书信后,在背面写道:“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以此来回敬了高欢。一计不成,高欢又把韦孝宽的侄儿押至城下,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向城内高喊若不投降,就要杀死他。韦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人有死难之心”,从而更加坚定不移了西魏士卒与城共存亡的信念。
高欢苦战了近六十天,丝毫不能撼动玉壁城。由于伤亡惨重,一筹莫展,加上天气寒冷,给养不足,消耗惨重。高欢“智力俱困”,只得班师晋阳。想到七万将士命丧城下,“聚为一冢”;想到原本凯旋后的庆功酒,将被讥讽声所替代;这种视觉上的血腥冲击和精神上的高压态势,使高欢愤恚成疾,一病不起。这时,韦孝宽又制造了高欢中箭身亡的谣言。为了稳定军心,高欢不得不带病“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这就是《敕勒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日食日,52岁的高欢发出“日蚀其为我耶,死亦何恨”的感慨,一代枭雄竟在窝火和重病中与世长辞。最终西魏以少胜多,并由此从弱走强,国力大盛,以西魏为基础建立了北周,又以北周为基础建立了隋,最终平灭北齐、南梁,结束三朝鼎峙。
有一个问题是,“博得后人极端的倾倒”(郑振铎语)的《敕勒歌》,到底是不是斛律金的首创?对此,《乐府广题》认为不是由斛律金所作,斛律金只是翻唱者。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大会上时讲话:“北朝的将军斛律金,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既“不读书”、又“不识文字”的斛律金,是不大可能创作出《敕勒歌》的,但他却是《敕勒歌》能够流传千古的最大功臣。宋代学者王灼《碧鸡漫志》就说,“金不知书,能发挥自然之妙如此”。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则评价为:“莽莽而来,自然高古”。元代著名回族诗人丁鹤年有感于此,乃赋诗一首:“神龙归卧北溟波,愁绝阴山《敕勒歌》。惟有遗珠光夺目,万年留得照山河”(《鹤年诗集》卷二《敬书宸翰后》)。诗中所说的“神龙”就是指神武帝高欢。很显然,高欢是想用这首歌颂家乡的歌曲以安定军心,激励斗志。但在客观上,使这首民歌得以记载并流传下来。
穿越1600年的历史时空,天籁之音《敕勒歌》至今仍传唱不衰。耐人寻味的是,大青山并没有因《敕勒歌》而名扬天下,而敕勒川却声名鹊起、名声大噪。但历来为兵家必争的大青山及其脚下的沃土敕勒川,饱经无数次硝烟烽火的蹂躏和沧桑岁月的洗礼,展现出的早已不是那水草丰美、天野相接、香气袭人、牛羊游动的亮丽风景,而是“大漠天低四野园,黄沙千里绝人烟”(余正酉《出塞绝句》)的悲催图景。进入新世纪,一场旨在恢复大青山生态外衣、重振绿水青山的战斗打响了,史无前例的生态建设大幕由此拉开。现在,走进大青山前坡150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四周的绿齐刷刷压过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历史画卷在新时代重新呈现,这或许是对千古枭雄高欢和一代名将斛律金的最大慰藉。我们还需做的是,深入挖掘隐藏在《敕勒歌》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敕勒川文化,让举世闻名的《敕勒歌》在其发源地真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名至实归!
民族宗教局 赵紫阳 供稿